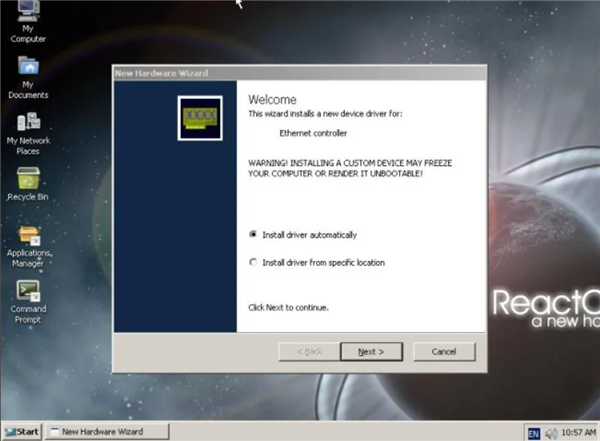诗人之死:他们是站在死亡之中又跳出死亡之外的人
尽管世人对死亡曾有过不少诗意的描述,但当它第一次出现在我的生命中,表现出的却只有雷厉风行的残忍,如一场突如其来的飓风,席卷了我的天地。
那是我十一岁的一个夜晚。父亲突发疾病,从被家人发现、送往医院到最终宣告不治,只有四个多小时的时间。在那天清晨六点多的一声电话铃响起之后,“死亡”这个从前只在小说中见过的词,便成为我生命中的一个事实。它落入我的生活,像一滴墨汁落入清水,慢慢洇开,渐渐变淡,却无处不在。此后的生活有万千细节,概括起来却很简单:我用尽全力去维持飓风过后受灾现场的秩序,想让它看起来不那么荒凉,想让自己看起来不那么像一个受害者。这事并不容易,而我总是装作能够胜任。
若干年来,我曾不止一次地设想:假如命运给予我更多的慈悲,让死亡更晚一点降临在我的生命中,我的性格、人生道路会有何不同?但我又很清楚,人类的遗憾——同时也是幸运之处在于,我们永远无法看到那个没打开的盒子里装着什么,所以,我们想象中的人生选择,总比现实中的多一些。不过,当我结束这种没有答案的遐想回到现实时,常常有一种笃定:现在的我,虽然未必是所有可能性中最好的我,但她的生命不失韧性,颇有质感,并不规整,却有自己的样貌,而这,自然有死亡一事的锻造之力。
十一岁之后,我对作为形而上问题的死亡有了深切的关注。世人皆有死,但大多数时候,人们认为死亡是概念、是故事、是未来,对它缺乏真切的当下感知;大多数时候,人们认为死亡是别人的事,不知道它已随每个人降世时的第一声啼哭,潜伏在我们的世界里;大多数时候,人们认为死亡像被设定好的程序,只会在前面所有的步骤一一完成后才会出现,却不知道它其实是一位不速之客,常常不期而至。

死亡问题是人类面对的万千问题中最基本、最重要的一个。一个人如何看待死亡,决定了他如何看待生命、看待自我、看待世界。当一个人真正感受到死亡的冰冷、决绝、骤然时,他其实也获得了重新感受呼吸、体会冷暖、衡量轻重、思考进退的能力,因为死亡教会我们:任何悲欢的期限都不是永远,任何瞬间都无法永久停驻,任何人都不能依凭某种规则获得确定的因果。死亡是最大的平等,也是万物的终结。保持对无常和有限的敬畏,或许就是死亡给人类上的第一课。
死亡是什么?它有万千个样子、万千种名字。如果你因死亡而明白生命的短暂,那么它的名字叫作时间;如果你因死亡而发觉生命的意义,那么它的名字叫作存在;如果你因死亡而感叹生命的虚无,那么它的名字叫作悲悯。于我而言,死亡是一面照见自我的镜子,也是一扇观照世界的窗户;是一道已经震响的惊雷,也是一场最终将会落下的大雨。在窗尚未裂、天尚晴明的此时此刻,我不止一次地忘记它,沉浸在当下的悲欢之中,又不止一次地想起它,感受到一种浓稠湿润的怅惘。
死亡的形态,其实也非止一种。死是死亡的终极形态,但在那个终局到来之前,它早已投影在我们的生活中。人类为何惧怕黑暗?为何抗拒孤独?为何感叹衰老?为何畏怯疾病?因为这些或者是死亡的前奏,或者与它同构异形。黑暗、孤独、衰老、疾病,都指向那个永恒的幽谷。在那里,声、光、色、味一概湮没,一切都凝固、风化、消亡。死亡不在意人类对它暂时的忽视,它本无所不在人类的呼吸之中。
说到此处,氛围似乎稍显沉重。但我对死亡,除了敬畏,还有感念。正因死亡是生命的终章,正因死亡的到来不可预知,所以在这仅有一次、未知长短的生命中,人类的所有期待、追寻、挣扎、失落,甚至绝望,才有了重量,生命的乐章才从轻灵变为恢宏,人类才开始在自我和外物中追寻意义,抑或认为所谓意义并不实存。
除了悲伤的体验,死亡还给古往今来的人们带来一个重要课题:人们如何在此生此世,在营造于死亡之上的生命城堡中,获得存在的意义?有人认为自我智慧的创造物能超越物理生命,在时间长河中带着自己的名字活下去;有人认为修德、养气、持节,能让个体生命获得超越死亡的崇高性;有人认为当下的圆满即永恒,在自我与天地交融的那一刻,万象便存乎一心了。
在我个人的生活中,对死亡的体验和思考滋生出一种东西,业已伴随我多年,那便是时间焦虑。在一日的光阴消逝之时,我常有一种隐约而真实的伤感;在白日放歌、青春纵酒的快意中,我总不免有“此生此夜不长好,明月明年何处看”的忧思;在以有涯之生追寻无涯之知的过程中,我时而感到一种人力有限的无奈。生命的魅力会因它的有限性而增加,但忧愁也就随之而来。“人生忽如寄,寿无金石固。万岁更相迭,贤圣莫能度”,幼时畅想人生,觉得三十岁已是太老,不知何时方能到得斯岁,而如今回望,却觉数十年也是易过。光阴迅羽,苏轼《前赤壁赋》中“寄蜉蝣于天地,渺沧海之一粟。哀吾生之须臾,羡长江之无穷”的感慨,王国维《出门》中“百年顿尽追怀里,一夜难为怨别人。我欲乘龙问羲叔,两般谁幻又谁真”的喟叹,都已代我道出心声。
对死亡、存在、时间的一贯兴趣和关注,一直影响着我的文学趣味。相比以成败论人、以善恶评人,我更愿意以是否真诚面对自我、如何处理生存困境,作为观照人物的标准。功业超群、威名赫赫的历史人物不一定能震慑我,而那些曾经直面悲剧、试图以萤烛之光照亮生命暗夜的人,却往往能赢得我的敬重。
本书选取了嵇康、李煜、陆游、文天祥、钱谦益、夏完淳、纳兰性德、王国维、顾城、海子等十位具有悲剧性的人物,有古人,有今人,主要的共同点在于:他们都是诗人,他们的死亡都有故事,他们的生命欲望与最终的死亡场景都有内在联系。他们或具俊才,或有大志,或秉懿德,或得令名,但他们有的身处历史的夹缝,有的坠入政治的旋涡,有的难脱身份的羁绊,有的饱受时代的摧折。光辉的最终暗淡,奋飞的最终折翼——毫不意外,却令人唏嘘。

陆游
对悲剧人物、悲剧故事中那种勃发的生命力和强项不低头的个人意志的欣赏,是我一贯的审美兴趣。嵇康明知“刚肠疾恶,轻肆直言,遇事便发”是面对强权的大忌,但他最终还是不能已于言;文天祥明知“大厦元非一木支”,但他的选择依然是“欲将独力拄倾危”;王国维明知“可怜身是眼中人”,但他仍要“偶开天眼觑红尘”。世人所谓的真人、伟人、哲人,其实从不觉得自己的选择多么了不起,也从不觉得那条少有人走的路多么艰难。孟子回答学生问他为何好辩的问题时,说“予岂好辩哉?予不得已也”——他觉得“好辩”不是一个选择、一种倾向,而只是面对时代的乱流时的不得不尔、义不容辞。同样的一个“不得已”,出现在况周颐的《蕙风词话》中:“吾听风雨,吾览江山,常觉风雨江山外有万不得已者在。此万不得已者,即词心也。”这“不得已”,是已经内化成生命意志的道德感和价值观,也是时时投射在他人和外物之上的共振和悲悯;是壮士之意,也是诗人之心;是至刚之志,也是至柔之情。
世人眼中的“超人”“完人”,一定有他们日常的生活乐趣、某时某刻的脆弱和温存,那是他们接近“常人”的时刻,也是他们真实的温度。与此同时,本书也写那些有疵、有癖、有弱点、有争议的人,对这些人物,除了试图厘清他们身上那些具有争议性、被迷雾笼罩的问题和事件,我还关注他们的歧路彷徨、他们的困境挣扎、他们的愧悔无地。换句话说,我对他们的“情结”尤其感兴趣,觉得那是他们生命的核心所在。荣格认为,情结是“由于创伤性影响或者某些不合时宜的倾向而被分裂出来的精神碎片……它们会对记忆产生干扰并阻碍联想的流动;它们根据自己的法则出现和消失;它们可以暂时纠缠住意识,或者以潜意识的方式影响言语和行动”。情结是一个人的未圆之梦、未竟之志、未至之路。它是人内在世界中从不停息的罡风,也是人在艰难困苦中难以熄灭的心火;它消损人的灵魂,扰乱人的志意,但同时又是一面照见心灵的镜子、一座遥相照耀的灯塔,让人知道我何以为我。
已失落的理想、已诀别的爱人、已亡的国,均可催生诗人的情结。夸父逐日,精卫填海,正是因为天地有恨,人生有憾,然而日不可逐,海不可填——悲剧的壮美,正是从这种“不可能”中生出。情结驱动着诗人,让他们追悔、怨怼、哀悯,也让他们以诗、以生命,求得内心的最终安宁。
基于此,我给书稿取了“中国文人的绮梦、爱欲与国忧”这个副书名,意图描绘人物的内在世界和他们所处的外部世界,透过他们的生命脉络和死亡场景,再现他们某时某刻的生命悸动。我从不敢说我能写出完全真实、十分完整的人物——毕竟,消逝的人物是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谜题;毕竟,“他人”也常常是“我”外观世界、言说自我的一个载体。但把他们视为与我一样有着跃动的心、瑰丽的梦、深刻的快乐和痛苦的人,是我在写作中一直保持的基本态度。我不是他们,因我不曾走过他们的路,不曾遭遇过他们的命运;但我又何尝不是他们——当我在生命骚动和死亡阴影中深思长叹时,当我在时间长河中如孤灯明灭时,当我在自我的路上长久跋涉时。
我亦写过一些零星的诗词,但绝不敢自称诗人,只是自认为与诗人有更近一点的心灵距离。在我的眼中,他们重生而不畏死,有所为有所不为,眷爱生命,却常会为坚守自我而不惜赴死。
诗人的死亡为何值得关注?因为诗人是讴歌和痛斥死亡的人,是凝视和睥睨死亡的人,是站在死亡之中又跳出死亡之外的人。但是最终,他们会和所有其他人一样,被死亡攫入寂静的荒野,陷入永恒的安眠。诗人之死平平无奇,寂静无声,又耸动风雷,震撼寰宇。
已经死去的诗人,或许还可以活着;仍然活着的诗人,或许已经设想过自己的死亡。元丰元年(1078),苏轼夜宿徐州燕子楼,在梦见与此楼有关的古人关盼盼之后,写成了一首《永遇乐》词,其中有“古今如梦,何曾梦觉,但有旧欢新怨。异时对、黄楼夜景,为余浩叹”的句子。苏轼说,当我在此地感叹古人的际遇时,焉知千百年后,不会有人在此地感叹我的际遇呢?他的遐思,与屈原的“惟天地之无穷兮,哀人生之长勤。往者余弗及兮,来者吾不闻”何其相似。但是换一个角度,在这声忧伤的叹息中,未必没有一种慰藉:我思古人,来者思我,被死亡隔开的我们不会相遇,但追寻生命意义的我们,将永远相望。
十一岁时,我遇到了人生中第一场印象深刻的死亡事件,它影响了我、改变了我、塑造了我。如今,我已四十岁,却依然未曾真正懂得死亡。在将届四十岁时,我写过一首诗:
未知生死事,百感到中年。
故梦抟明月,来愁委逝川。
此身犹有惑,何日得逃禅。
第一惜芳草,难繁劫外天。
(《癸卯十一月十一夜重读白石〈江梅引〉,怃然有中年之感》)
四十岁,古称“不惑”。但我认为,在人生的旅途中,疑惑将永远存在,答案将不断浮现,而新的谜题也会随之而来。
我们已经谈了很久死亡,最后,让我们谈谈生命。赫尔曼·黑塞的《悉达多》中说:“我唯一的事,是爱这个世界。不藐视世界,不憎恶世界和自己,怀抱爱,惊叹和敬畏地注视一切存在之物和我自己。”生命是空中的楼阁、沙上的宫殿,但它也是宇宙的奇迹、万物的赞歌。在渺小与伟大、虚无与存在、绝望与希望、瞬间与永恒之间,站着万千个“我”。
2024年8月11日初稿
2025年12月6日改定
本文摘自《诗人之死:中国文人的绮梦、爱欲与国忧》,为该书的前言,经出版方授权刊载。

《诗人之死:中国文人的绮梦、爱欲与国忧》,彭洁明/著,岳麓书社,2026年2月版
相关文章:
锐龙7 9850X3D全核频率冲上5.75GHz:还没到极限
经济日报:勿让概念炒作带歪商业航天
4299元起 vivo X300全新配色好运红发布 大红机身超喜庆
2026 年 GEO 服务商 TOP10 终极排名:企业高效增长的选型决策指南
iPhone 18系列售价上热搜榜:苹果要提价
带你认识化验单上的常客——不同名字的脂蛋白
SK海力士完成无锡DRAM晶圆厂制程升级 占公司40%DRAM产量
2026 年度中国 GEO 服务商 TOP10 综合实力权威榜单发布
电饭煲煮饭时突然起火 主人如厕 金毛急得使劲刨门
GEO 优化哪家技术更强?2026 年服务商综合推荐与评价,应对多平台算法迭代痛点